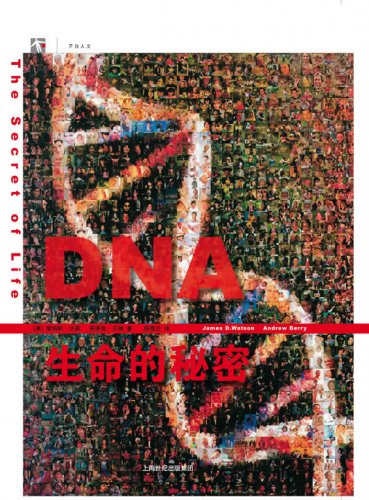- 注册
- 2014/02/13
- 帖子
- 3238
- 获得点赞
- 683
- 声望
- 113
- 年龄
- 61
自从上中医论坛以来,接触到很多中医人,也接触到很多中医爱好者,但更多的还是很多无助的患者,在现实中治疗不理想而被迫求助于网络论坛,但治疗效果却差强人意,这与现实中的情况基本吻合。现在的中医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呢?我发现无论是“学院派”还是“师承派”或是“西中派”(西医转中医)在论坛里讨论最多的还是《伤寒论》。有人说学中医必须要学《伤寒论》,因为张仲景就是中医的“祖师爷”。这话一点不假,我认为《伤寒论》是应该学,那毕竟是古人留下来的珍贵遗产,但现在有很多人,几乎是全天下的中医学子竟然把《伤寒论》视作圣书,视为打开中医学习之路的“万能钥匙”。由此还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的“经方家”或“经方派”。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了,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脱离实际、盲目崇拜的结果,注定是要失败的。举个例子: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思想一直被视为指导我军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思想,事实证明的确是有效的和成功的。因此在全党全军便产生了对毛的“全面肯定”和个人崇拜,这种罔顾事实的的盲目崇拜一直待续到全国解放和和平时期的国家建设阶段,结果给本已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遗憾的是,在毛死后竟然还有人提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提出却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结果两个“凡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堪一击,被迫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没想到的是,现在我们的中医界还在坚持“两个‘凡是’”, 这怎么会不令人担忧呢?
成也“毛泽东思想”,败也“毛泽东思想”。这句话同样也适合《伤寒论》。应该正确看待“毛泽东思想”,更应该正确看待《伤寒论》,肯定应该肯定的,否定应该否定的,这才是科学的、正确的学习方法。如果我们一味地墨守成规、不思进取,那么中医——祖国的医学瑰宝,就真的离消亡不远了。
就拿《伤寒论》里一个最简单的麻黄汤来说吧,有个中医学院的学生,结合《伤寒论》里对外感症状的描述,给她刚患感冒的对象服用,结果却越治越严重,最后又不得不让西医挂瓶输液去了,最后还落了个“中医就是靠不住”的名声。
相反,论坛里“医海之水源于泉”老师的一个案例:“活用麻黄汤,一剂保安康”,只加了一味“生地”,治疗感冒的效果却出奇的好(地址:https://www.tcmbe.com/threads/242849)。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同样是“麻黄汤”,面对同样的感冒,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呢?原因很简单,一味药(生地)的加入,就像是战争中军队的“粮草”一样重要。“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话说的多有哲理呀!而当时张仲景先师却没能悟到这一点,所以在治疗上难免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病状传变,再引入养阴生津之品,“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我在这里“批判”《伤寒论》,不是说它没有价值,而是认为它已经时过境迁不合时宜了,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伤寒论》里的治疗方法是缺少“人性化”的治疗方法。就拿一个看似简单的感冒而言,仲景过分强调药物的作用而忽视人体本身的体质因素。在这一点上,甚至都不如现在的西医。谁都知道,面对感冒(病毒),没有特效药,而西医采用的方法就是促进睡眠,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西药中的“复方氨酚烷胺”就有这样的作用效果。《伤寒论》里仲景所用之方,大都是阴阳不兼顾的“半成品”方。第二、《伤寒论》没有探讨致病的成因,也没有给出治疗思路,而是依据症状留下来的一些方剂,而我们现在大多数人还在用各种症状去套用《伤寒论》里的各种药方,显得多么机械、盲目和被动。这是造成中医界止步不前难有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三、患者群体质发生了大的改变。由于饮食结构和现代化药物的作用,当今人们的体质与古代相比已经大为不同,更多的是被西药(抗生素输液)搞得身体素虚,没有丝毫的抵抗力,而采用《伤寒论》里的方法,用药一味地攻伐,这与西医使用抗生素没什么区别。患者大都吃不消,其治疗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不知还有多少人在死读《伤寒论》?有多少人还在热衷于“经方”?又有多少患者被这“至高无上”的经典、经方搞得痛苦不堪?我说“成也《伤寒论》,败也《伤寒论》”还过分吗?中医界的人们应该醒醒了。
成也“毛泽东思想”,败也“毛泽东思想”。这句话同样也适合《伤寒论》。应该正确看待“毛泽东思想”,更应该正确看待《伤寒论》,肯定应该肯定的,否定应该否定的,这才是科学的、正确的学习方法。如果我们一味地墨守成规、不思进取,那么中医——祖国的医学瑰宝,就真的离消亡不远了。
就拿《伤寒论》里一个最简单的麻黄汤来说吧,有个中医学院的学生,结合《伤寒论》里对外感症状的描述,给她刚患感冒的对象服用,结果却越治越严重,最后又不得不让西医挂瓶输液去了,最后还落了个“中医就是靠不住”的名声。
相反,论坛里“医海之水源于泉”老师的一个案例:“活用麻黄汤,一剂保安康”,只加了一味“生地”,治疗感冒的效果却出奇的好(地址:https://www.tcmbe.com/threads/242849)。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同样是“麻黄汤”,面对同样的感冒,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呢?原因很简单,一味药(生地)的加入,就像是战争中军队的“粮草”一样重要。“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话说的多有哲理呀!而当时张仲景先师却没能悟到这一点,所以在治疗上难免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病状传变,再引入养阴生津之品,“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我在这里“批判”《伤寒论》,不是说它没有价值,而是认为它已经时过境迁不合时宜了,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伤寒论》里的治疗方法是缺少“人性化”的治疗方法。就拿一个看似简单的感冒而言,仲景过分强调药物的作用而忽视人体本身的体质因素。在这一点上,甚至都不如现在的西医。谁都知道,面对感冒(病毒),没有特效药,而西医采用的方法就是促进睡眠,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西药中的“复方氨酚烷胺”就有这样的作用效果。《伤寒论》里仲景所用之方,大都是阴阳不兼顾的“半成品”方。第二、《伤寒论》没有探讨致病的成因,也没有给出治疗思路,而是依据症状留下来的一些方剂,而我们现在大多数人还在用各种症状去套用《伤寒论》里的各种药方,显得多么机械、盲目和被动。这是造成中医界止步不前难有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三、患者群体质发生了大的改变。由于饮食结构和现代化药物的作用,当今人们的体质与古代相比已经大为不同,更多的是被西药(抗生素输液)搞得身体素虚,没有丝毫的抵抗力,而采用《伤寒论》里的方法,用药一味地攻伐,这与西医使用抗生素没什么区别。患者大都吃不消,其治疗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不知还有多少人在死读《伤寒论》?有多少人还在热衷于“经方”?又有多少患者被这“至高无上”的经典、经方搞得痛苦不堪?我说“成也《伤寒论》,败也《伤寒论》”还过分吗?中医界的人们应该醒醒了。